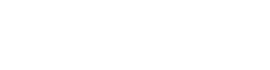在我的督导课上,我要求学生不要用「评价」的方式讲话。我发现这不太容易,他们一开口忍不住还是评价。怎样是评价,怎样是不评价,他们并不清楚。
一些人误以为不评价的意思就是不批评。他们选择赞美的语言:「我觉得你这里做得非常好。」或者:「我认为你是很优秀的咨询师。」但这还是在评价。
关于儿童教养的研究已经发现,「赞美」孩子并不总是有好处的。比如,有研究者让不同的儿童解数学题。解完一组简单题目后,研究者给了每名儿童一句反馈。对一些孩子赞美他们的智力:「哇,你太聪明了!」而对另一些孩子赞美他们的努力:「你一定平时很用功。」然后,研究者给孩子们更困难的一组题目。因为聪明而受到赞美的会更担心失败,他们倾向于完成难度较低的任务,遇到困难更难坚持,容易焦躁,甚至表现出自尊水平的下降。[1]——赞美他的天赋,居然会妨碍自尊!
乍一听这与我们的直觉相反。但细细一想,又符合我们的生活经验。
虽然赞美听上去让人舒服,但它仍然是一种评价。它把一个人捧到极高处,而后盖棺论定。可怕的就是这个「定」字。当我们受到赞美之后,我们常常会害怕自己配不上这样的赞美,会为此平添不少压力。出于压力,我们可能会更愿意重复相同的工作:反正我做这样的事情足以获得赞美,为什么还要冒险去探索更大的世界呢?更严重的情况下,我们干脆什么都不做了。「你们都夸我文章写得好,但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写出来的,如何好法?我怕再写下去就会露怯。」我们用放弃来回应赞美。
评价接近于一种定义性的表达。对于它,你只有接受或者不接受,但很难再产生更多延展性的探讨。它适合收进教科书里,作为结论。如果是现实的交流,就很可能造成冷场:你都已经下结论了,我还用说什么呢?从这个角度说,赞美甚至比批评更容易终止一个话题。批评好歹还可以反驳:你说我不好,我不接受!但是赞美怎么办呢?拒绝也不妥,但承接下去又实在没有发展余地。大家讨论得好好的,我突然来一句:「我觉得讨论很有价值,每个人都说得很好。」这会让场面的气氛骤冷。假如你接受了这句评价,你就很难接下去说。除非忽略这句话,大家才能继续聊。
不评价的交流方式是怎样的呢?它只关注具体发生了什么事,而不是进行抽象的判断,定义,甚至针对人的褒贬。一个不评价的老师,会这样问学生:「你最近常常不做作业,发生了什么呢?」而一个带有评价性的老师则会说:「你最近怎么老不做作业?」前者是在关心一件事的发展过程,而后者就只是在训诫。
后面这种情况下,老师根本不在意理由。他关心的只是对于学生的定性,而这件事他已经做完了。「承认吧!你就是个差学生。」仿佛是这样的潜台词。可以感觉到明显的拒绝。如果你是这个学生,只要低头认罪就好了,什么都不用说。除非你希望辩解:「不,不是那样!」可以想象,那将是一场不太愉快的争论。
通过前一种表达方式,我们则会更接近事件的真相。也许这个学生遇到了一些麻烦,也许他最近有了一些新的想法,或者他在用这种行为传达某种态度,或者还有其它的什么可能。当我们采用一种非评价的立场时,就等于为这些信息的流通创造了空间:「说吧,让我看到它,我对你经历的这些事感到好奇。」你无须辩解,因为根本没有辩解的对象。只需要单纯地描述你的经验就好,这是我们此刻关注的。
通过不带有评价的交流,我们在做一件事:描述经验本身。
经验的描述看上去最简单,但往往也最有力量。对于事物的认知和相互确认,远远比哪怕挖空心思给出的「赞美」更能表达出重视。对画画的孩子说:「这是你画的山,这是河水,啊,河水里有一只船,船上这个人是在钓鱼吗?哈,你还给他画了帽子!嗯,你在这边画了一个太阳,这边画了一个月亮,那是白天还是晚上呢?」对下棋的孩子说:「刚才这一步的时候,你选择和他兑子,他一下就没有子用来防守了,但是你的车和马有了配合。」你注意的是具体的过程。这些话里没有褒贬,但他们会感到自己做事被看见了。他们会乐于跟你讨论,也会更有兴趣继续做下去。
是的,通过不评价的交流,我们表达出对人的兴趣。在前面的儿童研究中,还有一半的结果没有讲出来,那就是另一些因为努力被赞美的孩子,会更愿意尝试新的挑战。一些研究者把两者的差异解释为:努力可控,而聪明不可控。但我还有另一个解释:努力是一个长期过程,并且充满了开放的可能性。当我们关注一个人的努力时,我们实际上是在说:嗨,你做的事我都看见了,而且我有兴趣继续看下去。
[1]Mueller, C. M., & Dweck, C. S. (1998). Praise for intelligence can undermine children's motivation and performance. JPSP第75期,33页
文章转自福建省心理学会
http://www.fujianpsy.com/xlyy_view.aspx?id=495
(编辑:心理学院2018级吴佳璐)
转载自公众号:李松蔚